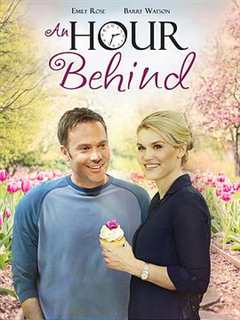《我爱迪克》:当“爱情神话学”遭遇“解构爱情狂”(6)
2023-04-26 来源:飞速影视
”二十岁出头时经历过的身份阵痛,在四十将近时又重新降临。这一次,文学超越戏剧,变成了更加直接而有力的表达方式。克丽丝的身份阵痛不再是女性或男性之间的矛盾,而是更加难解的纠缠与困惑:作为传统的被观看者和暴力承受者,女性该如何同时成为创作者?因为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观看和暴力。
于是,这作品成了一个艾玛自己书写的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十九世纪的艾玛不写作,她在现实中看到爱情的可能性就会抛下书本,去穿好看衣服,戴昂贵首饰,再把衣服首饰哧溜脱掉,以完成一个对想象的扮演。克劳斯也不是福楼拜,因为福楼拜对文字的痴迷甚于艾玛,以至于要狂呼“我就是艾玛·包法利!艾玛·包法利就是我!”。在几千年的文学史中,福楼拜们凝视艾玛·包法利,同时在她身上看到自己。但克劳斯,这位女性福楼拜,或者说二十世纪艾玛·包法利,显然超越了这种单纯的凝视结构。在看似单纯的迷狂下,克劳斯始终对自己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都有清楚的认识。任何试图概括或将之简单化的语句都是一种对赛博格精神的背离。这个赛博格女性显然无意扮演一个单纯的凝视者或创作者,也拒绝任何习见的被凝视的女性形象。《我爱迪克》仿佛是艾玛·包法利终于拿起自己的笔,开始记录自己,并观察起周围的福楼拜们。
于是,在重重悖论和阻碍中,女性怪物式的理论小说诞生了。
评论家称该书为“理论小说”,这个定义恰如其分:“理论成为小说情节的内在组成,在作者创造的虚构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克劳斯式理论小说最有趣的一点是,典故和理论之间不再由传统的文本间性或互文性串联(比如西尔维尔由妻子的婚外情想到包法利夫人或普鲁斯特),而是由精神分裂症式的巧合和无序相互串联,自由发展。从危地马拉叛军首领遗孀的绝食,到克尔凯郭尔,到德勒兹或汉娜·韦尔克,事物的联系即思维的联系。诸多引用和典故看似没有直接关联,却以一种混乱的方式将爱情和自我层层解构。克劳斯跳跃于各个理论之间。和西尔维尔不同的是,对于克劳斯来说,理论并非痴迷的对象,而是痴迷的手段。迪克也并非真正的痴迷对象,而是自身的映射。克劳斯将自己的作品移花接木成迪克的作品,更是临水照花的自我审视和关照。
“——这件事最终可以凝结成一句哲理:艺术取代了个人的想法。这句哲理非常适合用于父权制,我遵循了差不多二十年。也就是说:直到我遇见你。”
文本和典故的危险,克劳斯早在信中写到,于是典故并不仅仅是装饰,而成了男性知识分子叙事的象征,等待着被利用、被颠覆,正如暴君等待着覆灭,皇帝的新衣等待着被拆穿。而这一切“超越各种后现代修辞和话语”,终于指向了超越文本的“本质性孤独”,也正是克丽丝对迪克怦然心动的一刻,在他身上看到的特质。
相关影视

解构爱情狂
1997/美国/喜剧片
当爱情遇上科学家
2021/大陆/国产剧
爱情神话
2021/大陆/爱情片
我可能遇见了爱情
2023/大陆/国产剧
当我们的爱情散发香气时
2023/韩国/爱情片
爱情呼叫转移Ⅱ:爱情左右
2008/大陆/喜剧片
爱情的理解
2022/韩国/韩国剧
爱情奇遇记
2017/美国/喜剧片
合作伙伴
本站仅为学习交流之用,所有视频和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收集而来,版权归原创者所有,本网站只提供web页面服务,并不提供资源存储,也不参与录制、上传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www.fs94.org-飞速影视 粤ICP备74369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