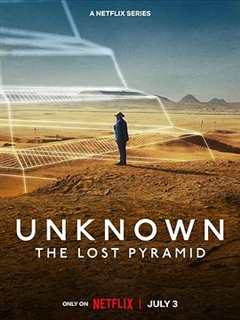锐评|刘悦琳:《人·鬼·情》:失落的女性与不知所措的女性主义(2)
2024-09-26 来源:飞速影视
如美国作家南希•弗莱迪所言:“当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女孩(即另一个女人)的时候,母女俩的命运就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了。没有人像母亲和女儿那样相互认同和相互依靠,也没有人像母亲和女儿那样相互限制。”波伏娃也曾说过“在男孩看来母亲是客体,在女孩看来母亲是自我”,女性认同对象始于母亲而止于母亲的历程足以说明母女关系对女性成长产生的影响将超过其它任何社会因素。尽管母亲在秋云的成长过程中几乎是缺席的,但童年时戏台上那一抹柔弱娇羞的倩影永远投射在秋云的女性意识之中,直至影片最后秋云仍无限憧憬对父亲说道“你演钟馗,我演钟妹,爸,你送我出嫁。”《人·鬼·情》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男性符号
秋云的第二次主体构建在于她和钟馗之间的生命关照。与不自觉的女性身份认同不同,秋云成为钟馗的过程是被迫的,是在“女戏子没有好下场”的悲剧预言下的悲愤出逃。秋云为了摆脱像母亲一样“不是被坏人欺负,就是天长日久,自己走了型”的命运,毅然表示“不演旦角,演男的”——由此,一个花木兰式的故事产生了。然而,扮作男性并不能帮助秋云逃出生天。因为女性雄化首先是以放弃自身性别角色而向男性角色规范认同为前提的,而一个人的性别及其社会身份是与生俱来、不可抛却的。古往今来“女扮男装”的戏剧故事之悲喜结局全在于扮作男性一度出人头地的女性是否还能回到她们终将面对的女人的现实中去。《女状元》中的黄崇嘏尽管高中状元、做官断案,一旦暴露女儿身后,只好弃官成婚;《繁华梦》中的王梦麟在梦中春风得意而梦醒后遁入空门;祝英台归家后仍不能摆父母包办婚姻的厄运;
而花木兰之幸在于“木兰不用尚书郎”。秋云决心扮成男人之后,男性的生殖器官出现在画面中,那是秋云与真正的男性永远的隔阂,象征着来自男性世界的高傲的拒绝。
主体构建不仅在于合一,还在于共生。与女性身份不同,秋云从未认为自己就是钟馗,钟馗在她的心中是以守护者的形象存在的。想象的界域产生于他者与自我的区分,他者的存在提示了本我的缺失,于是人开始渴望回到最初的圆满状态,渴望得到他者的爱。秋云在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后,屡次从母亲与“后脑勺”的苟且、二娃哥的背叛、张老师的爱而不能以及丈夫的失职中同时体会到女性的残缺与男性的孱弱,进退维谷之际,她在想象中找到了钟馗,实现了想象界与象征界的连结。
相关影视

悦来悦乐之醉爱之城
2018/大陆/剧情片
纠正措施
2022/美国/动作片
至今零差评的港产电影,堪称武侠剧的鬼斧神工,经典看不厌
0/大陆/综艺
玛德琳的玛德琳
2018/美国/剧情片
华锐嘎布
2011/大陆/剧情片
鲨卷风:锐利之心
2015/美国/喜剧片
淘宝女孩的好评爱情
2017/大陆/喜剧片
地球未知档案:失落的金字塔
2023/美国/记录片
合作伙伴
本站仅为学习交流之用,所有视频和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收集而来,版权归原创者所有,本网站只提供web页面服务,并不提供资源存储,也不参与录制、上传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www.fs94.org-飞速影视 粤ICP备74369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