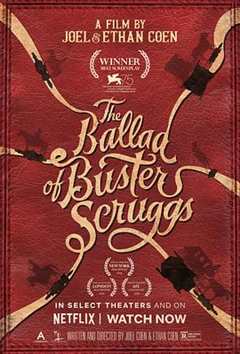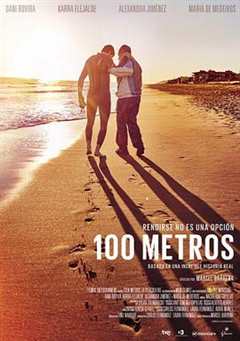普鲁斯特逝世百年:生命终结时,他迷人的敏感戛然而止(5)
2023-04-27 来源:飞速影视
所以,为了开始一段写作生涯,人可以暂时失去——也必然会失去——自己经历的一切,一切的失去都是为了在写作时追忆。除非作家提取出两样东西,明确地提出它们的关系,并用优美的文笔来书写它,否则,没有任何东西是存在的。对马塞尔,也对普鲁斯特来说,不直接叙述对象,而是以事后回想的方式来想象(回想)它,这是启动一段写作生涯的必由之路。在盖尔芒特家的藏书室,马塞尔思忖着他未来的写作生涯,思忖他将要写的文本是什么样的,他未来的全集又是什么样的。有一次,他无意中从书架上拿下了乔治·桑的《弃儿弗朗沙》,不觉记忆之门打开:那个早晨他已是第四次打开记忆了,每一次都是被物理感觉触发的,而每一次的记忆都清晰、鲜活,让他感到,那是处于时间之外的某种实在;每一个记忆都唤起了对另一个地方、另一事物的经验和感受:“我在当下和某个遥远的时刻同时感受到它们,直至使过去和现在部分地重叠。”
现实中的《弃儿弗朗沙》一书,把马塞尔送回到贡布雷的童年(“那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恬适、最忧伤的夜晚”)。随即,他又从这一思绪的回返折回,开始思考他作为作家的未来生涯,所有这些,他都是经由一本拿在手中的书所积极地想象着的,“今天,恰恰是在盖尔芒特家的书房,在这最晴朗和美的日子里,我重又见到这部作品,从而不仅使我以往摸索中的思想豁见光明,还照亮了我生活的目标,也许还是艺术的目标。”
就这样亦往亦返,向前并向后,两者既对立又统一,正如马塞尔的非写作的过去和他写作的未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而对立统一也一样出现在《追忆似水年华》的其他部分中,例如第四卷《索多玛和蛾摩拉》里,马塞尔在思考同性恋时对雌雄同体的论述:“女性人体中的某些男性器官痕迹和男性人体中的某些女性器官痕迹,似乎还保留着原始的雌雄同体的特性。”他发现,追忆性的写作,同样是一个既强力向前的探索性的动作(雄性)又不断后退的回归性的动作(雌性)。
普鲁斯特—马塞尔这类洞见,会直接让我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神秘的结尾,这个小说问世于普鲁斯特逝世三年后,菲茨杰拉德写道,盖茨比信奉码头尽头的一盏绿灯,这绿灯是“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
“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审美自我,是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我们早晚要看到,不具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人,在岁月的现实的压力下往往枯竭得最快。然而,马塞尔对作家生涯的沉湎,夸大的想象,就更多属于一种个人趣味了。这种沉湎和想象,表现了普鲁斯特自己的实情——他为了写作,早早踏上了一条跟死亡赛跑的道路,而这场赛跑他是不可能赢下来的。他明白这一点,可他还是进入其中,现实的、日常的书写行为,一面是用他剩余的生命转化的,另一面又被笼罩进了关于这个未来的文本的重重思想里。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名文《普鲁斯特的形象》里,用富于峥嵘的诗意的语言说出了他的印象:
相关影视

终结的感觉
2017/英国/剧情片
爱到世界终结时
2022/泰国/泰国剧
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
2018/美国/喜剧片
无名世界的终结
2021/日本/剧情片
盖布瑞案:消逝的小生命第一季
2020/美国/记录片
超感猎杀:完结特别篇
2018/美国/科幻片
生命中的百米
2016/西班牙/喜剧片
终结者:黑暗命运
2019/美国/剧情片
合作伙伴
本站仅为学习交流之用,所有视频和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收集而来,版权归原创者所有,本网站只提供web页面服务,并不提供资源存储,也不参与录制、上传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www.fs94.org-飞速影视 粤ICP备74369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