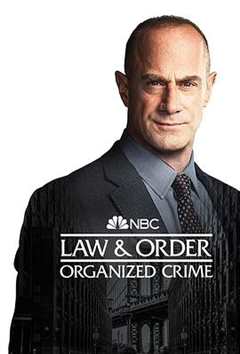旷野、城邦与迷宫:沃格林《秩序与历史》的三个地标(上)(7)
2024-06-16 来源:飞速影视
三旷野经验的复杂性表明,“存在的飞跃,在获得新的关于秩序之真理的同时,却无法获得全部真理,也无法建立一个终极的人类秩序。为秩序真理而战的斗争并未休止,而只是在新的历史水平上延续。”(卷二,第72页)旷野并非作为真理的超验秩序一劳永逸地实现的场所,旷野的开放性意味着它将面临更多危险。那些非真理的因素主要来自世俗生存,在写作前三卷时,沃格林也倾向于将宇宙论秩序视作这种飞跃的阻碍物。在以色列的两次旷野经验中,摩西被宇宙论秩序所纠缠,而以利亚为代表的先知则更多地受制于世俗生存。两者都阻碍着“存在的飞跃”的普遍意义的释放,但在后者的极端恶化情况,也即彻底的堕落与背离从而导致的无序中,超验秩序反而以更为纯净的形式从中突破。但很难说这是对超验秩序最好的处理方式,它倾向于瓦解整个世俗存在的意义从而导致灵知主义——在圣保罗那里,这种倾向变得更加强烈。
在关于古希腊的第二、第三卷中,一种有关均衡的意识已经开始显现在沃格林的论述中,城邦的经验特征使他花费了更多笔墨在那些阻碍着“飞跃”的东西上。对于旷野中的以色列而言,超验的存在秩序从未给予以色列人真正的安居,相反,安居是一种背离超验的诱惑,在动荡的年代这种诱惑就愈发强大,直至将先知们推至“最后的旷野及其自由”。与之相比,城邦中的希腊更为稳定,哲学家们并未试图在城邦之外的荒野上建立他们的秩序,他们的经验更为牢固地与城邦这一地理意义上的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实体相绑定。这种绑定使他们对宇宙论秩序的瓦解显得缓慢,并且使其更为纠结地处于与城邦内的人类共同体的关系中。与以色列先知相比,哲学家的克制使得那些张力的剧烈程度有所减弱,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们的精神焦虑:先知们可以出走,哪怕是从自身的生命中出走;但城邦对于哲学家而言依旧是一种无法最终逃离的东西,——在极少数的时刻才会出现有关“野兽”的不详符号——这是他们的庇护,也是他们的囹圄。
在哲学家之前,对于存在秩序的符号化由神话来完成,在赫西俄德那里,神话符号开始向形而上学符号过度:宙斯的狄刻战胜了旧神并建立起新的神山秩序。然而他始终是在世俗生存的领域中谈论着善恶,缺少以色列那种精神的紧张。但就其经验到世俗生活的无序,并试图引入超验神性这一点而言,他与以色列先知所从事的已经是同一种工作。之后,塞诺芬尼有意识地将其新神学与赫西俄德的新神话相区分,进一步拆解了神话的紧凑符号的意义——特别是其神学的普遍主义倾向。在塞诺芬尼那里,这种超验的存在秩序意味着人类精神共同体的可能性:“一旦有所发现,它就有权要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灵魂中去实现它;人的分殊化和他的天性的发现,是社会权威的一个来源”(卷二,第261页)。城邦因此成为其精神呼吁的社会领域。这种普遍主义并未完全扩及为“人”意义上的普遍——这一扩展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都以相当艰难的方式进行,就像在以色列的情况中那样——精神共同体的化身是城邦,普遍主义在这里首先意味着城邦公民的普遍性。
相关影视

天体的秩序第17话另一个愿望
2019/日本/日韩动漫
法律与秩序:组织犯罪第三季
2022/美国/欧美剧
哈利·波特:霍格沃茨学院锦标赛第一季
2021/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组织犯罪第二季
2021/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第二十一季
2022/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第二十二季
2022/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第二十四季
2022/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组织犯罪第一季
2021/美国/欧美剧
合作伙伴
本站仅为学习交流之用,所有视频和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收集而来,版权归原创者所有,本网站只提供web页面服务,并不提供资源存储,也不参与录制、上传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www.fs94.org-飞速影视 粤ICP备74369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