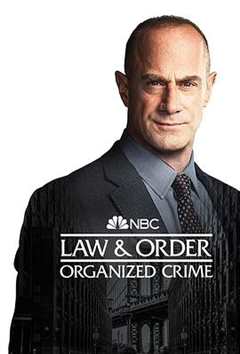旷野、城邦与迷宫:沃格林《秩序与历史》的三个地标(上)(8)
2024-06-16 来源:飞速影视
对城邦秩序的反思从来未曾以一种超出城邦的视角来进行,在超验的存在秩序偶然照入城邦的几个瞬间,人们想到的并不是另一片土地,而是如何以之革新城邦秩序。情况在巴门尼德与赫拉克利特那里有所改变。巴门尼德的“存在”是一个经典的哲学符号,它对应着人类一种名为“努斯”的官能。与此同时,赫拉克利特已将“灵魂”辨认出来,它处于追求智慧的过程中,并因其于智慧的这种关系而成为新的真理源泉。于是,“当把人性等同于在每个灵魂中共有的逻各斯的生命这种人的理念形成之时,城邦秩序就不再是无可置疑、终极的社会秩序了。”(卷二,第317页)尽管如此,这一发现在智者运动的冲击下面临危险,是柏拉图将其进一步地进行分殊,真正实现并且保留了“存在的飞跃”。
苏格拉底之死使得柏拉图意识到唯有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城邦的不良秩序才会真正得到修复,但需要注意的是,哲学家并非只是秩序的求索者,他深备一种只有高尚灵魂才具有的爱欲;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对智慧与秩序的爱,但在这种爱的名义下,属人的友爱共同体也得以形成。这或许是柏拉图使用对话文体的一个原因:“对话是智慧秩序的形式,与演说作为失序社会的象征形式相对。它恢复共同的精神秩序,这种秩序因为修辞的私人化遭到破坏。”(卷三,第62页)尽管对于柏拉图而言,所谓“共同的精神秩序”在后期从政治秩序中撤退回学园,但这种带有索居意味精神秩序依旧不断地被世俗的城邦生活所牵引,最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重新整合。
在《高尔吉亚篇》中,权威从雅典人转移到柏拉图那里,由于失去了与神同在的存在,雅典失去了其正当性。“人与社会的正当秩序是善在历史现实中的具体化。具体化必须由已经看到善并通过景象来指示灵魂的人来承担,即由哲学家承担。”(卷三,第98页)但在《国家篇》中,柏拉图暗示了哲学家无法摆脱的“意见”困境,尽管朝向的是超验的善,但他不得不与恶同行,这种同行甚至变成了一种义务。在《国家篇》开始,苏格拉底从城市走下海港,对公共宗教崇拜表示尊重,在他想要回到雅典之时,他被拦了下来:
他已经走下来,现在他所到的深处使他成为人群中的一个,他们当然是友好的,但是凭着人数较多而有着一种玩笑式的力量的威胁,并拒绝听从放他走的去劝告。在留住他的那个深处,他开始了探究;他在友人身上施加劝导性的力量,不让他自由地回到雅典,而是让他们跟随他来到理念城邦。路始自比雷埃夫斯的那个深处,不是回到马拉松的雅典,而是向前、向上走到由苏格拉底及其朋友们在他们灵魂深处建立的城邦。(卷三,第104页)
相关影视

天体的秩序第17话另一个愿望
2019/日本/日韩动漫
法律与秩序:组织犯罪第三季
2022/美国/欧美剧
哈利·波特:霍格沃茨学院锦标赛第一季
2021/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组织犯罪第二季
2021/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第二十一季
2022/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第二十二季
2022/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特殊受害者第二十四季
2022/美国/欧美剧
法律与秩序:组织犯罪第一季
2021/美国/欧美剧
合作伙伴
本站仅为学习交流之用,所有视频和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收集而来,版权归原创者所有,本网站只提供web页面服务,并不提供资源存储,也不参与录制、上传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www.fs94.org-飞速影视 粤ICP备743695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