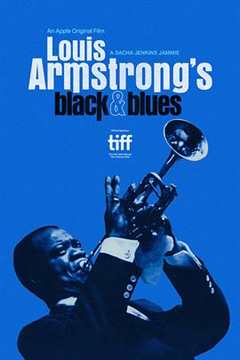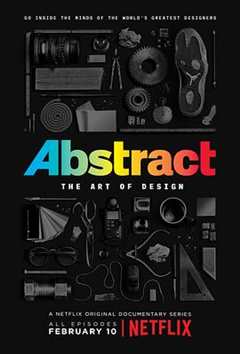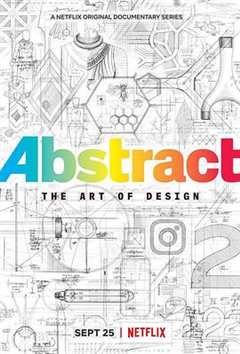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28)
2024-09-26 来源:飞速影视
长途步行迁徙、战场上的生死遭遇、小职员生涯的历练,这些都使得时代话语始终是穆旦写作的一条主线,构成了穆旦写作的基本底色。在作品修改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时代话语,穆旦显然是多有考虑。穆旦1940年代中段之后的《时感》《饥饿的中国》《世界的舞》《绅士和淑女》等,都可说是对于现实问题过于直接的处理。其中,长达7章的《饥饿的中国》,不同版本中的异文将近60条,多是标点、字词的异动,但也有数处涉及诗行的修改,如“纯熟得过期的革命理论在传观着”(《文学杂志》版)一行,亦作“论争的问题愈来愈往痛苦上增加”(《益世报》版)、“痛苦的问题愈来愈在手术桌上堆积,”(《穆旦自选诗集》版)。凡此,均显示了时代话语如何在穆旦笔下纠结不休的情形。此种纠结的情形正不妨从初作于1947年2月、又在《穆旦自选诗集》中有较多修改的短诗《他们死去了》来看取——也一并再来看看穆旦诗歌中较多出现、且具有前后贯联性的“上帝”/宗教话语:
啊听!啊看!坐在窗前,
鸟飞,云流,和煦的风吹拂,
梦着梦,迎接自己的诞生在每一刻
清晨,日斜,和轻轻掠过的黄昏——
这一切是属于上帝的;但可怜
他们是为无忧的上帝死去了,
他们死在那被遗忘的腐烂之中。
——初刊本(天津版《大公报》,1947年3月16日)
呵听!呵看!坐在窗前或者走出去,
鸟飞,云流,和煦的风吹拂,
一切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一切里面:
一个宇宙,睡了一会又睁开
奇异的眼睛,向生命寻求——
但可怜他们是再也不能够醒来了,
他们是死在那被遗忘的心痛之中。
——《穆旦自选诗集》版
时代话语与宗教话语的纠结,原本就是穆旦诗歌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于穆旦诗中宗教问题,王佐良当年有过判断:“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他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上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56]王佐良引述穆旦更早时期的诗作如《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之一》《悲观论者的画像》《我》,认为其中显示了宗教属性,而“他创造了一个上帝”“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等判断,又意在表明穆旦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诗人。
总体来看,就发生机制而言,穆旦诗中的宗教与现实始终有着莫大的关联。初作于1947年的《他们死去了》也显示了这一倾向。诗歌以“可怜的人们!他们是死去了,/我们却活着享有现在和春天”开端,其间涵盖了1940年代穆旦诗歌的一些核心主题,“大众”“死亡”“遗忘”“上帝无忧”等,诗歌写的是荒凉、颓败的现实场景,“为泥土固定着,为贫穷侮辱着,/为恶意压变了形,却从不碎裂的”(语出稍后的《荒村》一诗)无名者的死状。不嫌夸张,穆旦将自己的形象嵌入到了感时忧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谱系当中,但是,初刊本《他们死去了》的后半段导向了“上帝”:“他们死去了”,是因为上帝“无忧”,上帝没有给予关切——希冀“上帝”来拯救处于“不幸”之中的民众,其情感固然强炽,忧切固然深重,却大大地背离了中国的传统,这样的表述不能不说是非常触目。
相关影视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黑人形象与蓝调音乐
2022/美国/记录片
彬与瑛
2022/日本/剧情片
彬与瑛2017
2017/日本/日本剧
我的时代,你的时代
2021/大陆/国产剧
抽象:设计的艺术第一季
2017/美国/记录片
抽象:设计的艺术第二季
2019/美国/记录片
我在人艺学表演
2022/大陆/记录片
胜利的形象
2021/其它/战争片
合作伙伴
本站仅为学习交流之用,所有视频和图片均来自互联网收集而来,版权归原创者所有,本网站只提供web页面服务,并不提供资源存储,也不参与录制、上传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若本站收录的节目无意侵犯了贵司版权,请发邮件(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删除侵权内容,谢谢。)
www.fs94.org-飞速影视 粤ICP备74369512号